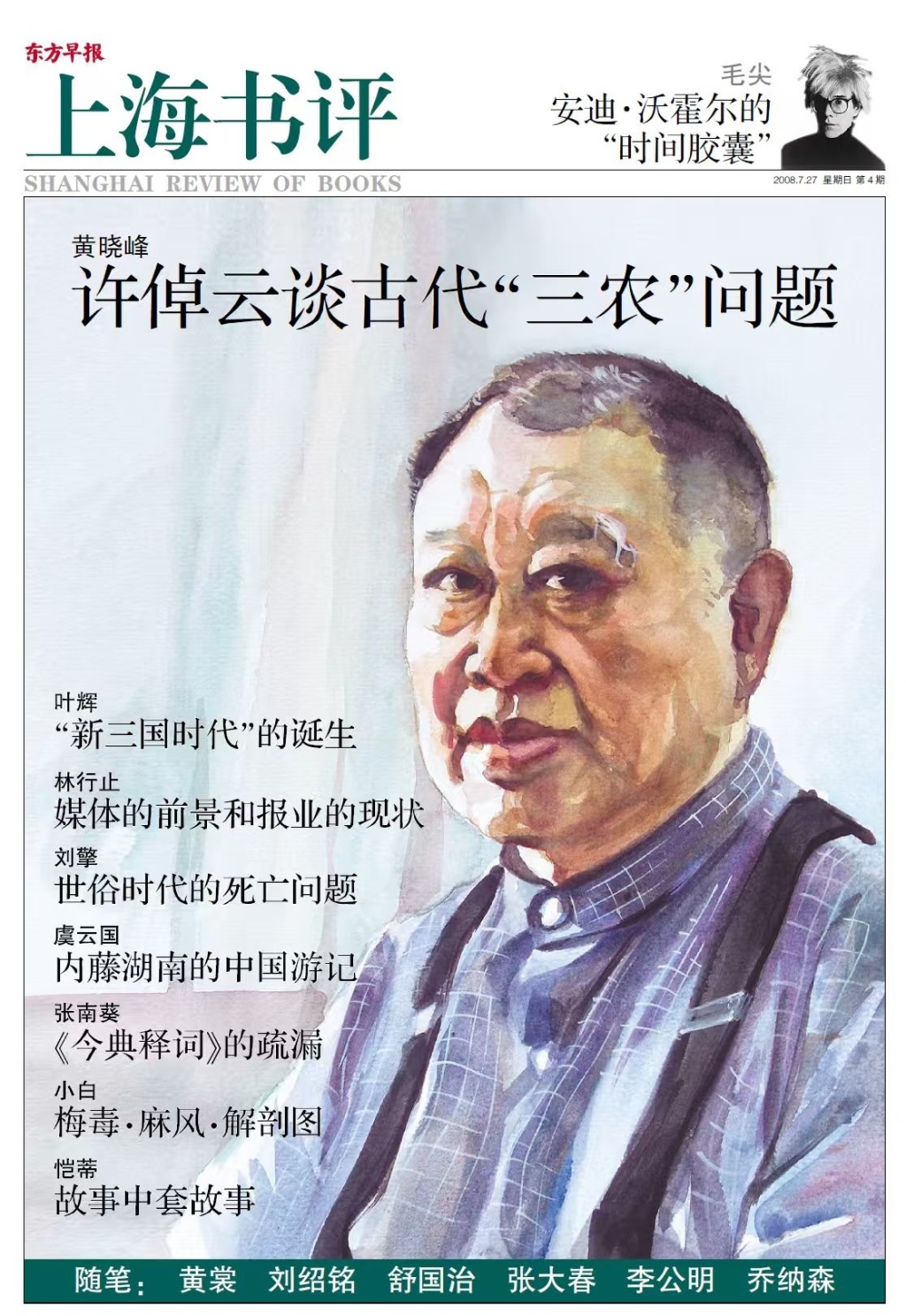
许倬云(李媛绘)
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于当地时间8月4日在美国匹兹堡去世,享年九十五岁。
2008年,许倬云先生作为嘉宾,在上海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揭牌仪式。借着这个机会,在许教授下榻的宾馆,《上海书评》对他进行了专访。也许是刚从苏北的盐城赶到上海,许教授谈的最多的,是国内目前比较关注的“三农”问题,这也反映了许教授对于现实的学术关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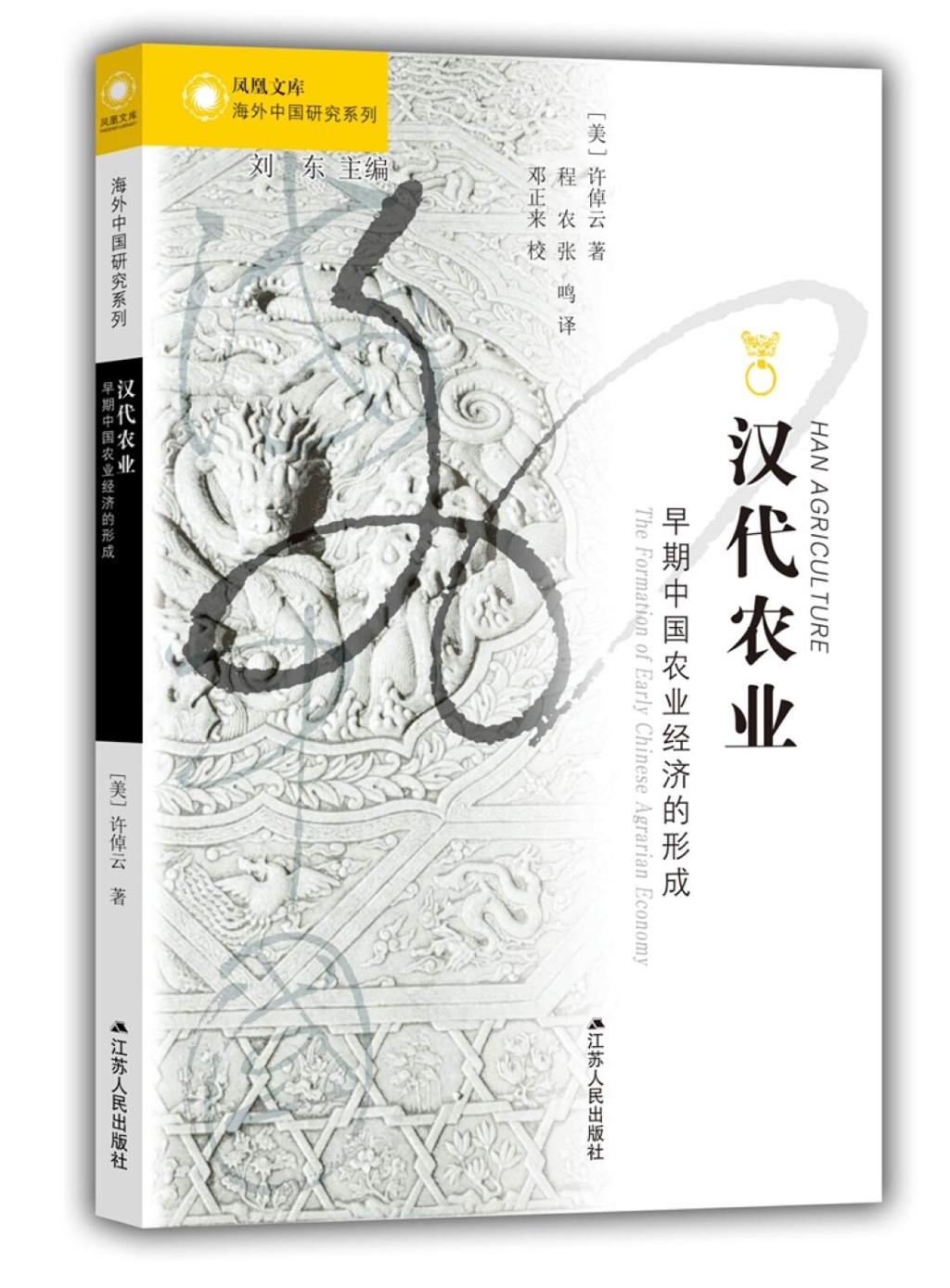
《汉代农业: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》,[美]许倬云著,程农、张鸣译,江苏人民出版社,1998/2012/2019年出版
中国古代三农问题
您早期学术的代表作是《汉代农业》一书,而且您也一直对农业很感兴趣,是什么原因使您关注农业问题呢?
许倬云:这是一个偶然的因素,这个题目到我手上是偶然的,因为西雅图的华大(华盛顿州立大学)有一批学者,要编一个汉代的丛书,分门别类,有个题目叫“汉代的农业”,这个题目本来是交给哈佛大学的杨联陞先生写的,杨先生不想写了,交还给他们。他们就叫我来写,我说可以呀。因为我在抗战期间颠沛流离,在中国农村里走过不少地方,别人是走路,我是坐在椅子上、坐在小板凳上、坐在石头上,逃到哪个农村,别人忙,我不忙,我不能做事嘛。我坐在那里看别人做活,所以通过那些农村啊,operation,整个操作过程,我看了不少,小时候看了不懂,长大了慢慢反刍就回来了。我就写一个精耕细作制度,从书本上找出精耕细作演变的过程,以及当中最大的转折点是汉武帝。从这个角度写,结果和他们丛书的体例是不合的。他们丛书的体例是希望有一本叙述型的东西,我变成这个分析型的东西了。
中国现在讲“三农”问题,古代也有“三农”问题吗?
许倬云:有啊,“三农”是套套相连啊。你不能只有农业,没有农民和农村;也不能只有农民,没有农村和农业。我们中国的“三农”问题发生困难,不自今日始。从近代的工业以及外来的机器产品进来,就把农村产品挤掉了,农村就凋敝了。所以我们的病根病得很久,费孝通先生的《江村经济》《乡土中国》,想乡土重建,尤其最后一部书,他是讲得很对,要让农村里的生产力不能只限于农产品本身,要有工业产品。但他并没进一步阐释拿什么样的工业下乡,于是乎在(人民)公社的时候,甚至于要拿土高炉下乡。河南农村那时是很落后的,为了救河南农村,就办个皮革厂了,办个印刷厂了,这些都是没根的,你拿城里的工厂到那里去,一点根都没有。所以我的建议是把农产品加工工业带到农村去。
从历史上看,从古代到现在,农村一直没有改变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?
许倬云: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每个农户、每个农家能够分摊到的耕作面积非常小。但是也不完全这样,我们是全劳力摆进去,我们耕地不足,就拿劳力来补它。我们是精耕细作,每一年最少有一个月大概无法耕作,但那个月,麦子也埋在底下了。
古代农业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是哪个朝代?
许倬云:人口少地方多的朝代,农业问题就解决得好。还有就是农业税少的朝代,汉朝农业税非常轻,十五赋一,后来还三十赋一。黄仁宇先生说的明朝,明朝财富很多,但是税赋制度都是放在农民头上,或者放在农业头上,工商业没有负担太多税,这时明朝民间可以很富,国家很穷。清朝亦复如此,他没有拿工商业的税收下来。康熙永不加赋是不加人丁税,土地税还在涨啊,而且等到地主拿到手上,他负的地税转嫁到他的租客上面去了。一直不应该有人头税,应该是生产税,生产多少,要拿产值纳税,不管工业、商业或农业。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为什么那么多,他没有别的路走嘛,他不能转换成工商业。日本人限制农民的数目字,由老大继承家产,老二、老三你漂流去,进城打工、做小商人、参军、做武士、做海盗、渔夫,都可以。中国农民全在土地上嘛,一个小面积生产量就是增加人手,他又分家,本来爷爷一百亩,儿子是三十亩,孙子是十亩。
那土地不够用怎么办?我们没有侵略冲动吗?
许倬云:我们没有侵略冲动,我们安土重迁。土地不够用,我们搬家啊,从北方往南搬啊,不断往南搬,我们这个地方(上海)就是搬出来的啊。
农村的福利问题如何解决呢?
许倬云:农村的社会福利怎么做?是拿国家公权力还是社区公权力(来做),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。我们看见选出布什的人,忍了多少痛苦,要熬他八年,发动莫名其妙的战争,拿本来几千亿的钱去挥霍光了,竟然还不想下台。一整套的东西需要重新整顿,国家公权力该怎么做,该怎么摄取,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。昨天我还和盐城师范大学谈,那里不是滩涂地嘛,就是冲刷淤积起来的地嘛,地是沙,地是咸,向来产量不高。他们有个任务,怎么利用这个土地,他们就跟我讨论,怎么做?我就告诉他们,这个不能单单从土壤一条路下手,你要从生态环境下手,此其一;第二呢,你要从重整社区、农工合作下手。你要从整体循环下手,拿肥料来中和沙里的碱,有计划地培养耐碱的草,拿沙地的土壤种根茎类的植物……在台湾,以前拿甘蔗做糖,做了糖运出去,所有的农户都被雇佣,农户拥有自己的土地,他可以和糖厂签约,他的甘蔗是固定送给糖厂的,糖厂先支付他钱,预付一半。他家里的其他人,工厂雇佣做工人啊。这个我就亲眼看见了,一直到国际糖价跌了,别处糖做的便宜了,甜菜糖打倒了甘蔗糖,他们才不做了。今天台南公司还在养猪,我们今天吃到的最好的猪肉还是台南公司的呢。我跟盐城人讲,你可以做个实验,弄个一万亩,你肯定赚钱。建设社区我有个口号:无弃地、无废料、无闲人、工商结合、生态循环。这个社区不能很大,我的理想中,这就是社会福利的单位,比当年的公社合理点吧。盐城可以从一万亩发展到三万亩地,假定说有三千人,这三千人有五个自然村,每个村有教育,有医疗所,有工厂的单位,道路、能源、教育、医疗都在里面。
您怎么看农民进城?
许倬云:不进城啊,工厂应该下乡啊。把生产设备移到农村。
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住在城市里呀,比如美国。
许倬云:美国不一样,美国人少地多啊。美国开发期间,一块钱一百亩,土地哪里来的,都是印第安人的土地。欧洲一直是到近代化进城以后才往城里搬,现在也在往城外搬。美国拿城市分离出去,没有城市了,叫公路圈,都是边缘城市,没有核心的城市。现代化没有一定的模式,没有必要进城,像北京的错误是错到了极点,错到巨无霸。新加坡,一个新加坡市,造了十个卫星城市,每一个卫星城镇的人,基本上不要离开城镇,有工业,有商业,有生活需求的种种,不要开汽车,走路。所以新加坡规定,一辆车子进出城镇,一定要至少坐三个人。家乡稳定了,当然住家里好了。在家门口有事,有工作做,谁不愿意住家里啊。
黄仁宇的“数目字管理”
您现在经常给企业家做管理学的讲座,是不是研究方向有个从历史学向管理学的转向?
许倬云:其实没有,历史本身就是人类的综合经验。综合经验里面你可以提取很多的东西。对哪个有兴趣,就可以提出来做一个整体的观察。譬如我对管理学偶然有兴趣,我就可以拿文官制度来帮助管理的经验。等于一大罐汤一样,随便舀什么都可以舀得出,看你怎么用就是。
那么您觉得在历史上哪个朝代管理得最好?
许倬云:没一个管理得完美的,因为管理制度本身也有生命,它会由盛而衰。管理制度是个系统,在系统里面参加运作的是人。同一代人进入了系统,所以系统是为这一代人设计的,就像一个朝代的建立。但人本身有生老病死,第一批人零零落落走了,第二批人就会接上来,这中间就有改朝。第一批打天下的人这种特别的性格:敢冒险,相互能合作,第二批人上来就不一定了,可能就比较守成一点了。如果制度设计的时候,一个系统各个部门应当平衡、互相协助,到第二代可能就会互相抵制,所以这就是弊端的开始。另外一种可能呢,太平日久,那些个人,特别强有力的领袖,他的部门就扩大,就膨胀;比较弱一点的人,他的部门就萎缩。结构就改变了,所以有无数的可能发生,变化就可能衰退,因为无法协调,会造成冲突和抵制。Energe消耗掉了,它(系统)就瘫痪了。假如再有外敌和内部的灾难,这个文官系统没有办法面对这个难题的时候,不是造成革命,就是自身垮台。所以任何制度没有完美的制度,都在变化,在change。
您所说的管理学和历史学的结合,与黄仁宇先生所说的“数目字管理”方法有什么不同吗?
许倬云:有不同的,他相信数目字。管理不一定是数目字的,管理是一个全面的事情,数目字只是一种资料而已。而且他误解了,中国不是没有数目字,中国的数目字的类别、收集方法和西方不一样,不是没有。黄先生讲话过激,因为他是军官转业,他抗战期间做军官,那时候没有什么制度不制度了,一个师,两天打下来,可能三分之二打光了,那就换一批人进来,哪有制度不制度啊?他看惯了那种打烂战的办法,他以为是天下管理都如此。所以黄先生的经验是有他特殊的地方,而且他也不是从正规的一般的学校毕业,他是半路出家的,所以他的观点很聪明,他的《中国大历史》写得非常好。他是个很了不起的史学家,他有很深刻的洞察力,insight,深刻、敏锐的观察,他写文章的体例也很好,他拿明朝的一年来写,一则那一年是个转折点,二则那一年的横切面代表了明朝的发展,前面怎么结束了,后面怎么开展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体例,今天没有人做同样的写法。体制是条船,开船的是人,好的水手在急风暴雨中能够稳定,坏的水手,一个小浪头就翻。
知识分子的定位
您以前写过不少关于古代知识分子的文章,您觉得现代的知识分子该如何定位呢?
许倬云:现代的中国,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知识人员,不是知识分子,他掌握的是一些特殊的知识,用来作生产和服务用的。本来,知识分子的知识是为了使人生丰富,既有批判性,又有创造性的。在今天,这一部分工作是丢在文化人身上。而文化人在整体结构上常常是弱势。古代的“士”已经没有了,因为我们的饭碗都交在人家手里了。
萨义德在他的《知识分子论》中提出知识分子应该边缘化,保持对现存体制的批判性。您怎么看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?
许倬云:不叫边缘化,应该叫脱钩。(批判性)曾经非常强,从清朝末年开始,一直到抗战,都很强。但抗战以后,资源不够,政府变成唯一的解决吃饭的东西,生活资源掌握在政权手里。现在没有办法超脱了。古代的知识人可以回家种田,有五六亩地就可以吃饱了。我们可以公平点说,那时候一支笔两本书就可以解决了,学富五车,现在的铅印本,排一排,也就是一书架,很多人都能做到。要是用U盘的话,最小的U盘还摆不满。今天的知识太多了,但是今天也有公众的知识储蓄的地方。为了获得知识,古人和现代既有方便也有困难,扯平。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是因为工商业发达,知识商品化,所以他们老早老早就消失了,美国没有知识分子。英国还有一点,德国还有一点。今天,大多数人,包括教授在内,他的独立性跟着获得而减低。知识的商品化,权力的集中,这两个构成了知识分子的消失。有没有转机的可能呢?有转机,知识的传播,以前靠平面媒体,平面媒体你要送到报纸,送到杂志,美国的报纸就是三家,他可以独占你的,报纸可以选择你的文章的。现在在网络上,你弄个blog,什么人都可以看见。我在美国,美国的教授们有一个特殊的权利,他不能开革你,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吃他的饭不听他管,这一点是大陆没有的,台湾地区也没有的。但是美国的媒体受大老板掌握,他不会用人写文章批评他的。我的独立性是这样表现的,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地区改革开放的时候,我和一批朋友,全心全意投入,推动改革开放,推动政府的改革,非常兴奋。我们那时碰到台湾地区经济快起飞,所以报章杂志不要看人脸色吃饭,杂志本身有足够的财源,他们撑得住。所以在那种情况下,我们意气风发,我们有自己的园地,可以讲改革学制,要实行民权,要废除“老国大”代表。我们天天吵啊,吵得热闹得很啊。我人在美国,文章发在台湾省,那时候也没有email,电话念啊。畅所欲言的标志就是吵架。
转载请注明来自北京夏犹清建筑装饰,本文标题:《纪念许倬云先生|许倬云谈古代“三农”问题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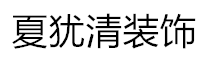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 京ICP备2025104030号-1
京ICP备2025104030号-1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